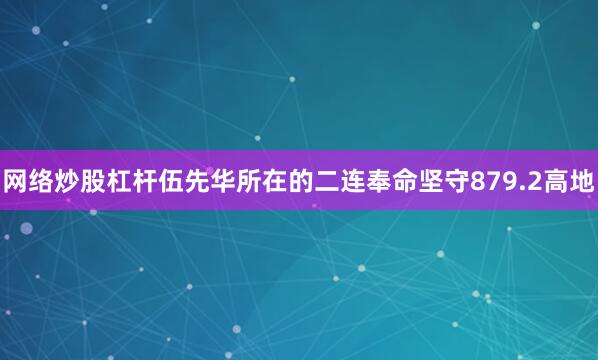一份 “通共” 名单,蒋介石拿什么抗衡毛泽东?
自1949年以来,学术界便围绕着一个核心议题展开了持久而热烈的探讨。
这一问题是:国民党装备精良的正规军人数达到八百万,而中共的土八路却只有百余万兵力,且武器简陋,缘何最终败局尽显?
有学者提出,国民党军队因派系林立,彼此难以相容,导致在战斗中难以形成合力,统一战线难以构建,最终导致了惨痛的失败;与此同时,另有学者着重指出,国民党在经济政策上屡次失策,特别是其推行的金圆券政策未能有效抑制通货膨胀,进而引发了民心的动摇,民众对国民党政府逐渐丧失了信心。

这些观点无疑各具其合理性与依据。但须指出,中共的胜利并非单纯依赖于武器之力,其根本在于那坚定不移的信念与信仰。
在潜在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国民党似乎陷入了被动与挫败的境地。无声的“攻心战”往往比硝烟弥漫的战场更为关键。
众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积极响应中共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纷纷选择投诚,此举极大地缩短了统一战线的进程。

“世间岂有不通共之人?”
网友对国民党内部结构松散、内奸横行的讽刺并非无中生有。
诸如“龙潭三杰”力挽狂澜,拯救上海中央的历史事件,亦如国防部作战厅的郭汝槐,他巧妙地获取并传递了大量的军事机密情报至延安,此类英勇事迹不胜枚举。

然而,诸如熊向辉与郭汝槐之类的个体,不过是一众小人物,而真正隐藏在国民党势力内部的巨头,乃是一批掌握重兵的地方军阀。诸如被誉为“小诸葛”的白崇禧以及“西北王”胡宗南等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1949年1月,随着中共胜利的曙光初现,国民党已无力扭转战局。
在此情形之下,毛泽东借助与苏共联络员奥尔洛夫——化名为捷列宾——的渠道,向斯大林呈递了一份内容详实、极富机密的情报,该情报揭示了国民党部分高级将领与中共之间的秘密联系。

奥尔洛夫回忆道,数月之前,毛主席曾特意要求身边的秘书与警卫人员暂时退下,以便与他单独会面。在这次私密交谈中,毛主席透露:“国民党将领白崇禧曾秘密与我们取得联系,表示若收到任何指示,他都将无条件遵从。于是,我们通过地下党组织向他传达了一项特别要求:一旦解放军越过长江,向武汉发起攻势,他必须保持原地待命,不得轻举妄动。”

电报中详细记载了众多国民党内部高级将领与中共秘密联络的诸多细节。
名单上诸多显赫的名字映入眼帘,诸如白崇禧、西北王胡宗南、汤恩伯、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华北战场上的英勇将领傅作义、第四绥靖区司令刘汝明、湖南地区的实权派程潜,以及四川地区的军阀刘文辉等。

此电报后续在《党的文献》上得以公开发表,鉴于该刊物的文章须历经严谨的审查程序,方能对外公布。
此外,《党的文献》作为官方出版物,其背后坚实依托于中央档案馆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因而自然而然地拥有了相当的公信力。

在1949年的这一关键历史节点上,毛主席之所以向远隔重洋的莫斯科透露国民党高级将领与中共密切联系的信息,其背后原因主要有二:首先,苏共作为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而中共则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这一关系,中共理应向其汇报工作进展。
固然,这仅仅是显露于表面的动机;实则,毛主席的深意在于借助这则机密信息,争取苏联的援助,进而促使苏联彻底摒弃对国民党的支持,以避免其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一旦“通共”名单公之于众,倘若蒋介石健在,定会怒不可遏,暴跳如雷,甚至可能破口大骂。
白崇禧、卫立煌等人物究竟如何与共产党取得联络,并在蒋介石的严控之下成功脱身?接下来,我们将聚焦这些将领的生平,深入挖掘他们政治立场转变的深层原因。

卫立煌,安徽合肥之籍,早年投身军旅,曾身负重任,担任孙中山先生的贴身警卫,竭诚守护其周全。
得益于孙中山的赏识,卫立煌逐步得到晋升,于军事界迅速脱颖而出,历任师长、军长及司令官等众多要职。

在抗日战争的尾声,卫立煌受命担任中国远征军司令一职,他凭借卓越的指挥才能,成功开辟了中印公路,由此声名鹊起,跃升为备受瞩目的军事英才。
然而,在解放战争的烽火中,卫立煌接连采取的行动,不禁激发了国民党内部的疑虑与不安。
1948年1月,他继陈诚之后,担纲东北地区“剿匪”总司令之职,统率55万雄师,却屡次以种种借口为托辞,对蒋介石关于打通沈阳外部交通线的命令置若罔闻,拒不执行。

与此同时,卫立煌屡次回绝了派兵增援被围困的锦州,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终被林彪的“101”部队所攻克,导致国民党在东北的主动权随之尽失。
随着辽沈战役的落幕,众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卫立煌产生了深深的疑窦,他们纷纷指责他可能是中共秘密发展的特殊党员。情绪激动的他们甚至一度强烈要求以极刑来平息公众的愤怒。
鉴于战局愈发严峻,蒋介石权衡再三,意识到若对大将施行极刑,恐令麾下将领心生畏惧,遂决定仅对卫立煌进行撤职,并随即展开调查。

1955年,卫立煌重返京城,昔日的挚友周恩来和朱德亲临车站,热情相迎。毛泽东亦破例设宴款待,以此表达对卫立煌的诚挚欢迎。此后,卫立煌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辽沈战役的分量自是不言而喻,然而,卫立煌是否真的被策反,故意按兵不动导致锦州失守,这一问题至今仍笼罩着一层迷雾,尚未有定论。
显而易见的是,卫立煌与中共的关系密切程度颇高,此乃无可争议的事实。

1985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中记载,地下党员赵荣声于1938年2月遵照上级指令,前往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麾下开展统战任务,彼时他担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直至1941年,赵荣声方才重返延安。
凭借深厚的白区工作经验,刘少奇在洛阳向赵荣声严肃指出:“你务必坚持长期潜伏,静待良机,同时时刻准备随时撤离。”

该书进一步阐述,1938年四月,卫立煌应毛泽东之邀,特地绕行延安,展开了为期三日的拜访。在此期间,平日里不喜饮酒的毛泽东破例之举,与卫立煌共留下了八幅合影,这一幕充分彰显了两人之间深厚的情谊。
传闻中,忻口战役之际,卫立煌三次与周恩来唔面,倾诉心迹,渴望融入中共,然终未达成所愿。
正是在这一阶段,卫立煌被赋予“七路半”的别称,此名寓意着他与加入八路军的距离仅差毫厘。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卫立煌的倾向共党的行动多少受到了一定的遮蔽,蒋介石对其并未有过分责难。
自然,蒋介石并非等闲之辈,他在卫立煌周围巧妙地部署了特务以实施监控。蒋介石曾对特务明确指示:“卫立煌在军事上有过人之处,但对于政治事务却不太熟悉,你们需时刻对他进行严密监视。”
1941年,蒋介石将卫立煌调任河南,担任省政府主席一职,同时剥夺了他的上将军衔,此举无疑削弱了他的军事权力。这一举措引起了周恩来代表中共方面对卫立煌的歉意,他诚挚地说:“你的遭遇,实乃我党的牵连所致!”
1947年,当卫立煌身处欧洲时,他悄然与法国留学期间担任左派领袖的汪德昭取得联系,并向中共发出了诚挚的电报,表达了他的心愿:“我渴望尽早终结内战,并立志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翌年一月,蒋介石派遣卫立煌负责收拾陈诚遗留的残局。卫立煌遂任命汪德昭担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以便与中共展开有效的沟通与联络。

显而易见,与蒋介石相比,卫立煌展现出了更为亲近中共的姿态。
首先,卫立煌并非源自浙江之地,亦非黄埔军校出身,他在国民党体系之中,并不被视为蒋介石的亲信。
第二,卫立煌在国民党中长期郁郁不得志,生活相当压抑,加之他并不认同蒋介石的政治理念,因而逐渐倾向中共一方。

在深入探讨卫立煌的生平之后,我们的关注点将转移至蒋介石的得力门生,那位颇具争议的将领——胡宗南。
胡宗南的才干屡遭非议,此情形实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众人对这位统领着近二十万雄师的将领,竟未能击败仅有三万人的西北野战军感到困惑。关于这一困境,众说纷纭,以下为几种可供参考的解释。首先,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胡宗南的军事才华常受到批评,似乎他并未真正领悟兵法之精髓。其次,有观点指出,鉴于其特殊党员的身份,甚至有人怀疑他存有“通共”的倾向,这无疑为其蒙上了一层阴影。
胡宗南出身于贫寒之家,早年他的思想倾向明显偏向左翼,因此对左翼群体抱有一定的同情。与国民党内其他成员的生活态度相比,胡宗南显得尤为特立独行。他并非热衷于财富的追求,坚守道义,拒绝接受任何不义之财,对女性亦无特殊兴趣,他心中唯一的深情寄托,便是他的妻子叶霞翟。
在黄埔军校求学期间,胡宗南与同窗好友关系匪浅。外界普遍流传着他有可能投奔中共的说法,这主要得益于他与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之间的深厚友谊。胡公冕作为共产党员的身份,早已为人所共知。国民党当局曾试图对胡宗南进行逮捕,但贺衷寒挺身而出,为他进行了有力的辩护。鉴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胡宗南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以此作为摆脱外界猜疑的有效途径。

在进攻延安的征途中,发生了一件令人费解的插曲。毛主席由于未能及时撤退,与胡宗南的部队相距仅一个小时的车程。然而,让人困惑的是,胡宗南在行军过程中步伐异常缓慢,战斗的节奏时而急促,时而松懈,让人难以捉摸其决策背后的逻辑。在青化砭战役中,副旅长周贵昌回忆道:“在我们尚未抵达青化砭之际,便已接到情报,称前方可能有伏兵埋伏。他随即向胡宗南发去了电报,寻求指示。”

面对伏兵暗伏的险境,胡宗南却在电报中对周贵昌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你过分胆怯,畏葸不前,丧失了军人的勇猛气概,必须遵照原定计划继续北进,迅速夺占青化砭,否则我将以通敌的罪名追究你的责任。”周贵昌虽感无奈,却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然而,部队最终遭遇了覆灭,这惨痛的教训无疑极为深刻。

历经一年的漫漫征途,胡宗南的举动犹如无的放矢,频繁调动兵力,却始终未能掌握解放军的行踪,反遭连连伏击。尽管俗语有云“吃一堑,长一智”,但胡宗南似乎未曾从挫折中汲取教训,这不禁令外界对其动机生疑。

“肩负重任,统帅军队时间最长,对国家军务的延误最为严重。”然而,外界对胡宗南的弹劾之举,最终因蒋介石的力保而未能达成预期效果。蒋介石似乎很快意识到了自己在任用人才上的失策。
郝伯村,昔日国民党高级官员,曾言:“蒋公晚年鲜少提及黄埔系学子。”此语透露出,胡宗南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已变得异常尴尬。

谈及胡宗南在军事领域的成就,其评价尚存争议,难以一概而论。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的秘书熊向晖曾是一位共产党员,这一历史事实不容置疑。熊向晖的党员身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早在1937年12月,当时“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团长李芳兰便曾亲自向熊向晖提出质疑,询问其是否为共产党员。

对于这些情况,胡宗南似乎并未过分介怀,反而挺身而出进行调解。在熊向晖晋升为机要秘书之后,李芳兰再度提出质疑,但胡宗南仍旧坚信不疑。即便胡宗南的特工机构接到了匿名举报,指控熊向晖为“间谍”,他对此亦只是采取了压制的态度。

熊向晖曾言,在他看来,胡宗南更似一位“夏伯阳式”的将领。夏伯阳,这位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由白军转变为红军的杰出将领,在熊向晖的比喻中,成为了国民党内部进步分子的象征。他认为胡宗南对中共并非全然排斥,同时他亦无意背叛蒋介石。

在回顾上述背景时,我们不妨提及,中共之所以在胡宗南与卫立煌周围部署特工,实因看重他们倾向左翼的思想。至于白崇禧的情况,则显得更为复杂,主要意图在于利用他与蒋介石之间的裂痕,以期实现拉拢的目的。至于程潜等地方势力,他们如同诸侯般敏锐地洞察战局走向,主动宣布投降,赢得了良好的起义声誉,这无疑是一种高明的策略。
正规的配资平台有哪些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配资怎么开户12.订正(dìng)
- 下一篇:理财配资平台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涌现